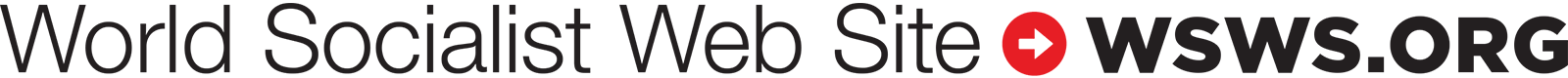譯者:孫訥
本文由周世瑀提交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她現居台北,在雪菲爾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
由工人、學生和青年等所組成的捍衛巴勒斯坦運動,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進行。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全球團結運動的怒火一致指向帝國主義政府的罪責,這些政府持續提供武器、資金,並使以色列遂行在加薩的種族滅絕。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國際團結,不但史無前例地引發民眾認識巴勒斯坦和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並且引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憤怒。
以色列在加薩厲行種族滅絕已超過9個月,但只有少數台灣工人參與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有些人意識到美國帝國主義的角色。他們從反戰的立場,中譯調查報告、訪談、評論等,讓大眾得知在巴勒斯坦所發生的事。有另一些人舉辦音樂會、公開會議等,引起對種族滅絕的關注。還有些人組成了「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這是一個由5個團體組成的非正式聯盟,他們提出4項訴求,並呼籲團結起來、線上聯署。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已有超過60個團體參與支持聯署。
聯署的具體訴求,可以歸納成以下內容
- 台灣立法委員應堅守國家的人權價值,「停止媒合軍火廠商與台灣企業」,以及「對以色列進行人權與人道倡議」。
- 外交部應停止援助以色列。
- 經濟部應公開台灣涉及以色列軍武貿易紀錄;並禁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資金。
- 政府應堅守「台灣的立國價值」,不使台灣捲入大屠殺之中。
雖然參與聯署者確實可能對巴勒斯坦感到同情,但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所提出的主要訴求卻會讓大眾感到困惑。顯而易見,該連線的訴求隻字不提台灣所支持的美國帝國主義。更未解釋為何之前向來「堅守立國價值」的台灣,突然「背離」自身價值、轉而支持以色列。而且,聯署中「台灣拒絕成為種族滅絕共犯(complicity)」之說,尤為醒目。
所以你搞懂了。因為以色列的冥頑不靈,才會發生侵犯人權及種種暴行。即使如此,工人可以經由人權倡議,和以色列討個公道。但沒有人會認為,工人可以經由向德國第三帝國倡議,阻止納粹大屠殺。同理,我們無法經由倡議,進而終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或者以柴契爾夫人所說的「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回應南非的種族隔離。
「左右」結盟的陷阱
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是個由立場對立的勢力所組成的「左右」聯盟。發起團體之中,其中之一是捍衛移工權利的組織,他們反對台灣與中國的資本主義政黨;以及幾個團體在政治上分別支持台灣執政的民進黨或中國共產黨。
支持中共的團體之所以支持這份聯署,是基於自身的史達林主義與機會主義考量。中國僅次於美國,是以色列第二大的貿易夥伴。自從中國於1992年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後,就如同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2022年所述,雖然「兩國相距6,437公里之遙」,中以關係卻能「互利共贏」。簡言之,「中以關係蓬勃發展」。
以色列海法新港,是由中國國營企業上海國際港務集團所經營。作為通往中東的海上門戶,以及一帶一路的其中一環,該港口每年吞吐量為「186萬個20呎標準貨櫃」。中國企業持續建造以色列主要基礎設施與交通項目,包括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以及臺拉維夫輕軌系統最主要的部分。
這解釋了為何新華社在加薩種族滅絕發生9個月後,還繼續宣揚「兩國方案」的幻想,並描述加薩種族滅絕是「巴以衝突」,或是「加薩衝突」。
於此同時,支持民進黨團體(以下簡稱獨派)因其親帝國主義立場而聞名,也就是只有在「美國說這件事是種族滅絕,這才叫種族滅絕」。但他們在促成這次的「左右結盟」最為積極。
由於獨派以「促進人權與自由」名義伸出橄欖枝,另外兩派自然接受。但很少人想到:(1)為何工人必須將「反對」加薩種族滅絕的立場,限縮在線上聯署、記者會、新聞稿、公關手法,或者是對美國的兩個附庸國的道德呼籲?(2)為何需要「左右結盟」來完成由一個非政府組織就能完成的事,有鑑於獨派經營許多人權組織和媒體?(3)消弭政治分歧,促進團結,究竟對誰有利?
由於獨派主導「尋求共識」,所以聯署的措辭不可避免地體現出「進步」外表下,所隱藏的台灣國族主義偏見。若要理解為何支持巴勒斯坦的團結與壓迫者國家的國族主義水火不容,我們就必須探討台灣的角色,它在冷戰期間與冷戰後,如何成為美國的前線國家以及附庸。
台灣訓練薩爾瓦多處決隊領袖
這幾十年來,台灣與美國所支持的極右翼政權合作無間,厲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這種合作可追溯至1966年世界反共聯盟的成立。該聯盟於1967年在中華民國台北舉行首次年會。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表示,這是場「自由與奴役之間,歷史性的鬥爭」,他曾在中國大陸領導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中國革命後流亡至台灣。他堅稱「自由世界的人民」絕對不能「各自為政,冒著遭個個擊破的風險」,反而應該採取協同行動,打造「自由世界的團結」、擊潰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
中華民國於1971年遭逐出聯合國,大部分西方世界的國家遂逐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自此以後,國民黨政權利用世界反共聯盟,作為連絡美國所支持的拉美極右翼獨裁政權的特殊管道。
國民黨政權很樂於經由世界反共聯盟的分支,拓展「自由」至拉丁美洲。被選中的薩爾瓦多軍官會由台灣支付所有費用來台,在政治作戰學院裡學習「非常規戰爭、審訊,以及反恐戰術。」
其中一位校友是達布松(Roberto D’Aubuisson),他是薩爾瓦多處決隊的首領、中央情報局線人,並於1984年成為總統候選人。他是個在薩爾瓦多內戰(1979-1992)期間殺害超過75,000人的戰爭罪犯之一,受害者包括許多婦女、兒童。
由於在審訊時以噴火燈對付政治犯,以及下令殺害羅梅羅主教(Óscar Romero)達布松因而惡名昭彰。
美國詩人福雪(Carolyn Forché)的著作《凡你所聞俱為真實》(What You Have Heard Is True)是她在薩爾瓦多期間的回憶錄,裡面講述了平民遭到強行綁架,以及失蹤者的悲慘遭遇。他們最後出現於「屍體堆中、太平間、路邊,以及海灘。」
福雪解釋處決隊如何用紀律約束隊員,以使群體逍遙法外:「當一個人加入成為處決隊時,他一生都在處決隊。如果你退出,你可能會透漏口風,沒人希望日後遭人指認罪行。所以首次參與行動時,其他處決隊隊員會試驗新人,讓他在眾目睽睽下強暴受害者,並砍斷受害者身體某些部位。他們想看新人有無膽量。之後,他就和其他人同罪,這時他就能成為隊員。」
為何每個處決隊的受害者,都必須遭到肢解,並在極度痛苦中死去?福雪手指出:「處決隊隊員必須對每樁謀殺集體負責。因此,一個人強姦,另一個施暴,其他人則用刀劈,以此類推。直到無法判定何種行為導致死亡,這樣隊員們在共同罪責下,相互包庇。此外,當死亡無法使民眾感到恐懼,他們會變本加厲。不但要讓人看到自己會死,而且是鈍刀慢剮而死。」
雷根總統任內,美國每天浥注薩爾瓦多軍隊150萬美元。台灣統治精英完全知悉薩爾瓦多國家及其處決隊所犯的罪行。國民黨喉舌《台灣評論》稱這種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為「反共的自由之路」。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孫運璿於1981年在世界反共聯盟大會解釋道,雷根政府對「共產主義」態度並非「被動遏制」,而是「積極消滅」,這對自由世界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對台灣由衷感激者又豈止達布松一人。日後成為薩爾瓦多軍隊總司令的中校蒙特羅薩(Domingo Monterrosa Barrios)1978年於政治作戰學院接受訓練。他在1981年下令進行厄爾蒙左提大屠殺(El Mozote massacre),殺害超過1,000名薩爾瓦多平民,其中幾近半數為兒童。
根據安德森(Scott Anderson)與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合著的《深入聯盟內部:揭露恐怖份子、納粹與拉丁美洲處決隊如何滲透世界反共聯盟》(Inside the League: The Shocking Exposé of How Terrorists, Nazis, and Latin American Death Squads Have Infiltrated the 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書中提到蒙特羅薩說過:「我們最佩服的是台灣政府對人民的控制。假如我們能夠在各個領域都組織一個政治作戰單位,我們就能從共產主義擴張之下,贏得這場仗。」他還補充道:「在瓜地馬拉,由於台灣人做了類似的事,所以瓜地馬拉人現在學會怎麼應用。我們還學到怎麼向平民展現自己,並獲得支持。」
台灣在瓜地馬拉種族滅絕的罪責
國民黨認為在台灣訓練瓜地馬拉軍官,是為美國帝國主義効力。由於中美洲靠近美國,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尤為看重此地,認為它是拉美政治「穩定」的關鍵所在。瓜地馬拉民選總統阿本斯(Jacobo Árbenz)於1954年遭中情局所策劃的政變推翻後,美國遂介入該國內戰(1960-1996)極深。
台灣和專制政權的結盟也得到回報。中華民國於1971年10月25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失去其常任理事國席位,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瓜地馬拉議長桑多瓦爾(Mario Sandoval Alarcon)在1971年10月28日訪台,重申他對台灣的支持,他日後成為瓜地馬拉副總統,任期為1974年至1978年。
桑多瓦爾曾多次造訪台灣,以加強極右翼政權之間緊密的「兄弟之情」,這些政權在各國經營世界反共聯盟分支。瓜地馬拉市處決隊指揮官之一的拉米雷斯上校(Elias Ramirez)曾擔任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館聯絡人。在此之後,瓜地馬拉派出大約「50名至70名」軍官來台學習政治作戰與國民黨信條,「唯有和敵人一樣殘忍」方能克敵致勝,正如《深入聯盟內部》一書所述。
師法國民黨政權,瓜地馬拉軍政府視不支持國家的人為「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學生、教師、知識分子、記者、牧師、工會成員、農民與原住民。
根據受聯合國所託,瓜地馬拉歷史澄清委員會在1999年報告書《瓜地馬拉:沉默的記憶》所載,該國內戰期間(1960-1996)估計有20萬人遭殺害或失蹤。若依據《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行公約》定義,這種國家所犯的暴行,已然構成種族滅絕罪行。
歷史澄清委員會調查顯示,身受酷刑時或遭謀殺前,常見女性遭強暴,它的目的在於摧毀受害者的「尊嚴」。這些針對平民的罪行,並非個別「害群之馬」所為,大約93%的違法行為都可以歸因於國家暴力。相較之下,左翼游擊隊的違法行為大約只有3%,其餘的4%則是一些不明組織或個人所為。
報告並指出,雖然瓜地馬拉軍中的「國防參謀總長」有責任承擔這些違法行為,但最終的政治責任必須歸於「歷任政府」,因為決策係「政府高層根據國安原則所為。」
就像薩爾瓦多一樣,台灣積極參與在瓜地馬拉的種族滅絕。據馬歇爾(Jonathan Marshall)、史考特(Peter Dale Scott)與杭特(Jane Hunter)合著的《伊朗門事件的連繫:雷根時代秘密小組與隱匿行動》(The Iran 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一書所言,退役的美軍將軍辛格萊布(John Singlaub)「以雷根名義在海外發言」,他後來成為美國世界自由委員會的創辦人,該組織是世界反共聯盟的美國分支。他於1979年與1980年會見瓜地馬拉總統盧卡斯. 加西亞(Fernando Romeo Lucas García)與其他政府官員。
當他回到美國,辛格萊布呼籲「對處決隊應表達同情理解」,因為盧卡斯. 加西亞政權在瓜地馬拉「促進人權的努力」,使他「印象深刻」。根據《深入聯盟內部》所述,雷根於1981年1月掌權後,處決隊的行動遽增。
即使聯合國所委託的報告中顯示,對馬雅人的種族滅絕是「瓜地馬拉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一頁」,鐵證如山、無可辯駁,但台灣的統治精英對其罪責卻沉默至今。
台灣志在成為種族滅絕者
民進黨於2000年5月上台就急於向美國展現自身的「用處」。美國總統小布希於2003年3月17日要求時任伊拉克總統海珊和他兩個兒子,在48小時期限內離開伊拉克,否則美軍將採取行動。一天後,陳水扁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火速支持即將發生的侵略,向伊拉克發出最後通牒,台灣成為唯一一個跟從美國行徑的政府。即使美國並未提出要求,台灣卻向美國空軍開放領空。
在美國主導的入侵發生後,民進黨政府經由其前線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積極向美國國會遊說,要求派遣台灣海軍陸戰隊至伊拉克作戰。
2004年5月美國國會台灣連線(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共同主席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以及成員瑞恩(Jim Ryun)向美國眾議院提案,要求總統小布希派遣台灣海軍陸戰隊至伊拉克。該提案聲稱,台灣向來與美國一樣熱衷「在全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並期望台灣能「與美國並肩作戰」。他們認為,台灣應獲准參加「全球反恐戰爭所組成的國際同盟」,並派遣其「35,0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前往伊拉克。部署台灣海軍陸戰隊,「可以減少非自願美國駐軍人數的需求,並對整個美軍產生積極的影響。」
然而在2004年6月,美國國務院東亞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明確表示台灣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不會受到歡迎。這場「反恐戰爭」的戲碼因而戛然而止。
我們有必要檢視,英美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前,是誰成為美國價值的受害者,而台灣卻自願為侵略戰爭效命。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1990年8月至1991年1月)後,聯合國調查小組在1991年3月10日至17日間造訪伊拉克。據其報告,該小組發現,伊拉克社會面臨一場「接近末日」的狀態,社會基礎設施、公衛系統、工業、城市等等,幾乎摧毀殆盡。然而,美國和英國卻拒絕該小組所提之請,即「取消聯合國對伊拉克的制裁」,以「防止疫病、飢荒問題」。結果是對伊拉克的制裁延續至2003年5月22日,這阻礙了電力、水資源、輸送管線、污水及交通等諸多系統的重建。
為加劇伊拉克人的苦難,甚至連廣泛應用於淨水的氯和明礬,也遭禁止進口。伊拉克人幾乎無法取得安全飲用水、衛生設備,或藥物。醫院根本無法治療飽受營養不良與疾病所苦的兒童,像是原本可以預防的痢疾、腹瀉和霍亂。即使有了藥物,孩子一出院就又喝到受污染的水,因而再次生病。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歐布萊特(Madeline Albright)在1996年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脫口而出,50萬伊拉克兒童死亡的「代價」是「值得的」。
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在2005年發表一篇研究,名為〈伊拉克兒童死亡率與制裁的關聯〉(Sanctions and childhood mortality in Iraq),研究表明「1984年至1989年每千名出生嬰兒的死亡率為47/1,000,但1994年至1998年則上升至108/1,000」。換言之,每10名伊拉克嬰兒中,就有1名在1歲生日前死亡。在世紀之交,伊拉克嬰兒與兒童的死亡人數就達到100萬人。
美國政府於2005年提出「薩爾瓦多方案」(the Salvadoran option)。正如《新聞週刊》(Newsweek)在2005年1月7日所言,美國派遣特種部隊至伊拉克,「支持、培訓精心挑選的伊拉克庫德族佩什梅加( Peshmerga )戰士和什葉派民兵,以打擊遜尼派叛亂分子,及其支持者」。由於軍隊與這類小隊行動消耗美國彈藥庫存,所以在同年,美國轉而向台灣要求補充彈藥。民進黨政府對美國心領神會,出於對處決隊的「同情理解」,將這座前處決隊小島改裝成死亡工廠。台灣政府自2005年至2009年間,向美國提供5億發5.56mm與7.62mm子彈。
如果你認為子彈威力不及迫擊砲彈、大砲砲彈、火箭推進榴彈、詭雷或手榴彈,大錯特錯。正如《紐約時報》在2009年8月19日一篇報導中解釋,過去半個世紀醫學研究數據顯示,子彈所致的傷殘,使「約1/3的傷者」死亡。上述種種彈藥則是使「5%到20%的傷者」致死。
台灣黑暗的歷史,影響現今深遠。2023年,在台北舉行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40週年慶祝晚會上,時任總統蔡英文就表揚這個前線組織,該組織試圖將台灣與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事綁在一起,並得到華盛頓支持。她表揚該會在海外一同「守護台灣」,並在「台灣隊」的成功中厥功甚偉。當天與會者之一博騰(John Bolton),就是伊拉克戰爭主要的策動者之一。
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夕,博騰向巴西外交官布斯塔尼(Jose Bustani)施壓,要求他放棄派員到伊拉克檢查化學武器的計畫,否則會危及家人。據英語媒體《攔截》(the Intercept)的報導,由於在入侵伊拉克前,這會戳穿關於海珊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謊言,所以博騰才會威脅巴西外交官:「我們知道你孩子住哪。」
自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以來,博騰代表著民進黨統治下的台灣所極力逢迎的社會階層。這才是台灣統治精英真正的「立國價值」。
國族主義助長分歧
讓我們回到原來的主題。在2024年5月15日巴勒斯坦浩劫日(Nakba),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的獨派發起者在台灣立法院外抗議,要求以色列停止對加薩發動戰爭。台灣的英語官媒「TaiwanPlus」概括獨派之於巴勒斯坦的情感與同情,「巴勒斯坦的建國之戰,和他們自身的奮鬥產生共鳴,由於鄰國中國宣稱擁有台灣主權,並經常威脅以武力佔領這個自治的島國。」
其中一位抗議者表示,台灣人與巴勒斯坦人一樣,一直面臨來自其他國家,試圖「剝奪他們國家認同」的生存威脅。
這並非獨派首次看到巴勒斯坦與台灣在追求建國之路上,因外部干涉而受阻的「共通點」。在2023年11月的抗議活動中,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發起團體之一台灣人權促進會於演說中,對比以下兩事:國民黨政權在白色恐怖時期(1947-1987)之於台灣平民的暴行,以及以色列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他並呼籲,「基於台灣所堅持的民主價值」支持巴勒斯坦。
在進一步討論前,有必要解釋什麼是「白色恐怖」(1947-1987)。國民黨政權在1945年10月從日本手上接管台灣,起初被視為解放者,受到台灣人的歡迎。然而,就像他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官員普遍腐敗、惡名昭彰,行徑猶如土匪。他們視曾在日本軍事統治和殖民佔領下的滿洲和台灣的華人為「皇民」或「漢奸」,充滿鄙夷。這種專制與傲慢引發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憤怒,他們赫然發現國民黨行徑猶如「征服者」。
國民黨政權於1947年鎮壓了在台灣反政府的抗暴行動,殺害或監禁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內戰中戰敗後,蔣介石帶著約200萬「外省人」(也就是跟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平民或軍人)撤退至台灣。其中包括許多貧窮工農受徵召進入國民黨軍隊,他們被用來當對付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炮灰。到台灣後,則是在建設社會基礎設施時遭到剝削、被當作廉價或可以棄若敝屣的無工資勞動力。
隨後,國民黨在1949年至1987年實施戒嚴,這是二十世紀史上最長的戒嚴之一。就像國民黨在中國的所做所為,國民黨在台灣也是「一視同仁」的壓迫者。在此期間,但凡與身在中國的父母或兄弟姊妹通信,都是叛國行為,可處以死刑。
民進黨和它的支持者很常將敵對的階級與利益混為一談,將所有外省人歸類為最具特權階層,認為他們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壓迫者」。
以此基礎,獨派遂將白色恐怖與加薩種族滅絕相提並論,暗示國民黨跟以色列很相似,是經由軍事力量與「定居殖民」來統治台灣的「外來勢力」。相較之下,民進黨歷任政府聲稱,他們統治台灣是基於「堅定的民主價值」。此說加強了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是存在這個島國的「外部」反動勢力;美國所支持的民進黨則是在台灣「本土」的「自由」勢力。
一篇在2024年6月6日的文章明確指出,所謂「支持」巴勒斯坦背後的動機。文章中提到,如同台灣建國一樣,巴勒斯坦建國也是項基本權利,而非他人贈禮 。文章接著擔憂,美國全球地位會因為支持以色列而「受挫」。隨著戰爭拖延日久,「中國的正面形象」因此強化。有鑑於此,「在巴勒斯坦問題保持沉默,無助於提升台灣國際地位。」
這種觀點本質上就是以自由主義掩飾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對於真正的團結運動者而言,最不應該擔心之事,就是維護帝國主義和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利益。
身為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益的表現,臺灣國族主義並非支持受壓迫民族的合法基礎。獨派和台灣統治精英皆不計一切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並因虛假的受害者身分,團結一致。
如同以色列的「公關」宣傳一樣,台灣資產階級聲稱,這個島國是面臨滅絕永遠的受害者。這種比喻被用來合理化台灣勾結「種族滅絕軸心」。反之,獨派則描述台灣是巴勒斯坦,或永遠遭受鄰國拒絕承認建國的受害者。這種觀點,很常用來為針對中國備戰背書。
建構台灣成為壓迫和侵略下的受害者云云,而非壓迫者或破壞勢力,歸根結底都是謊言,是政治反動的根源,是炮製出來供社會大眾消費。
美化台灣成為自由和民主的燈塔,遭受侵略和消滅,前述兩種看似對立的台灣再現,容易合而為一,成了永遠的受害者形象。獨派並非對抗台灣的政治體制,而是和資產階級相互呼應。他們與資產階級在台灣究竟應該扮演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歧見,常為策略性地選擇。隨著時間推移,以巴勒斯坦來比喻台灣的錯誤類比,變得流行,獨派則會進而趨向極右。
團結是指國際主義
恩格斯與馬克思於1847年發表演說,解釋為何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解放,具有國際性質。恩格斯作為一位革命共產主義者,他理解各國資產階級以國族主義作為分裂工人階級的手段。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工人必須消除國族主義,並揭發「自身」資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他警告:「當一個民族仍在壓迫其他民族,就不可能獲得自由。因此,只要波蘭未能從德國的壓迫中解放,德國就不可能獲得解放。」
馬克思進而闡述資產階級「兄弟情誼」如何阻礙國際工人階級的解放,他說道:
「各民族的統一與兄弟情誼是今天各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現在確實有一種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兄弟情誼。就是壓迫者對付受壓迫者、剝削者對付受剝削者的兄弟情誼。儘管一國之內,資產階級彼此雖有競爭與衝突,但他們還是聯合起來、建立兄弟情誼,以反對本國的無產者;同理,各國資產階級雖在世界市場互相競爭、衝突,但總是聯合起來以兄弟之情,對付各國的無產者。」
獨派拒絕承認,台灣支持在加薩所遂行的種族滅絕並非偶然。自1970年代以來,台灣持續助長種族滅絕,這比起「種族滅絕軸心」一詞的出現還要早了半個世紀。然而,台灣至今仍然以「自由和民主」之名,執意助長種族滅絕。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壓迫者聯合對付受壓迫者,「完全正常」的兄弟情誼。
「中國暴政」無法使酷刑、噴火燈審訊、致殘、強暴、屠殺、瓜地馬拉的種族滅絕、中美洲和伊拉克的「薩爾瓦多方案」,成為日常。中國也無法為捏造台灣的虛假和偽善故事,打造台灣成為「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捍衛者。中國更無法讓台灣人渾然不覺,這個島國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個反動、壓迫和次帝國主義國家。
正是台灣統治精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媒體,掩蓋了這個島國在國內外所犯下的罪行,讓台灣民眾對人類所受苦難漠不關心。這也解釋,為何獨派偏好台灣政治精英「基於人權和人道倡議與以色列往來」,而非選擇工人的獨立政治動員,這也是他們為何避而不談美國帝國主義。
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在聯署中所提的「台灣拒絕成為種族滅絕共犯」,並非要求終止台灣與以色列的共謀。而是為了開脫台灣,因為台灣從不承認自身在過往,以及現今參與種族滅絕的罪責(culpability)。
這種含糊不清的立場也受到支持中共的組織青睞,他們擺著空洞的「左派」和「社會主義」姿態。困在中國史達林主義的框架之中,這種路線傾向根本無法看見,解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工人的鬥爭,必須具有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性質。
總結,真正的團結運動,需要工人有意識地視國族主義為囚禁大眾的牢籠,它是資產階級壓制無產階級及解除無產階級武裝的工具。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場捍衛巴勒斯坦與所有受壓迫民族的團結運動,我們就必須與我們「自身」資產階級、以及各國的資產階級斷絕關係,並為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而戰,從而反對任何形式的國族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於其言論和實際作為已然彰顯,團結是指受壓迫者團結起來,而非與壓迫者團結,因此不留任何機會主義的空間。國際主義者有責任反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國族主義偏見、堅定地反對壓迫者階級,而且對身為少數立場毫無畏懼。要不,你是國際主義者,或你根本不是。如果你是國族主義者,不論你有多狡猾都無法偽裝。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特別感謝盧倩儀、John Smith與Chris Marsden提出初稿的修改建議。如有任何錯漏,責任歸於作者。